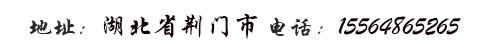回忆在南方农场奋斗的日子
|
南方农场15队往17队的公路桥 离开南方农场有四十多年了,期间与众农友也曾多次旧地重游过,对着曾生活过的地方心中感慨万千。 现今农场场部的变化真大啊!宽阔的水泥马路、排列整齐的路灯、高大的办公楼、绿色的文明生态园、园林式的休闲区、整洁的学生食堂、宽敞明亮的新校舍、丰富多彩的文化广场、各有特色的小食店和琳琅满目的小商店等等,几十年过去了,场部竞变得如此的美丽。再看看其属下生产队;位于中平地区的十五连和十七连都是南方农场属下最大的三个连队之一,青壮劳动力特多,以前每逢到了难得的休息日,农友们你来我往,或打打扑克,或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或在篮球场上见个高低,或随着琴声唱唱革命歌曲,好胜的男青年经常两个人面对面的用一根粗大的竹子互顶肚皮斗力气,或扳手腕,喝彩声与“加油”声一阵响过一阵,好一派热闹景象。可现况呢?十五连遍地瓦砾,形同被强烈地震洗劫过一样。以前拥有六栋占地面积约平方米的砖瓦平房,两栋砖木结构房,一间近百平方米用砖瓦建造的粮食仓库,近百平方米的木柱瓦面会场和托儿所等物业的十七连,现在只剩下一栋破旧不堪的危房,当年唯一的体育场地——泥土地面篮球场如今已是杂草丛生,知青们都回城工作了,很多老工人退休后都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活,当年老工人的子女们长大后都选择了到大城市工作,整个连队只剩下几位已退休多年的老人天天围坐闲聊。连队失去了人气、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失去了它过去的丰彩,她变得如此的荒凉,如此的寂静。几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想不到的是场部与连队之间的反差却是如此之大!看着照片中那些我们曾经居住过的房子现都成了一遍瓦砾,伤感之余又一次勾起了我对知青生活与工作的回忆; 冷冷清清的20队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十七日离开广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滚滚洪流,把我冲到了海南岛琼中县南方农场中平十二队,(建设兵团成立后编制为六师十一团十七连,以下简称为十七连)当年的十二月我便跟着有丰富经验的原中平作业区主任老工人庄达昌上大山伐木。在农场,我度过了整整八年的知青生涯,个中的甜酸苦辣也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但我与照片中部分已倒塌的房子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一九七一年,随着广东省各地知青及社青的不断加入,我们连队劳动力迅速彭涨,原有的房子(包括茅草房和砖瓦房)已无法满足居住的需求,为解决劳动力的居住问题,必须尽快增建两栋砖瓦房。为了建造这两栋房子,受连队领导委派,让我和老工人蓝春城同志带领几个人上山筹备建房用的桁条、桷子板、拉杆木、木门、门框、窗门、窗框、床板、板凳等等一切所需的木材。由于连队附近的“加福岭”经过历年的不断砍伐,适用的好木材已不多,我们只好到远离连队约七八公里远的“南茂苗寨”处再上深山去寻找,因路途太远,为节省更多的时间用于伐木,我们决定住在山上。 一天早上吃过稀饭后,我们打起背包,拿上一些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和伐木用的大刀、木锯,到大伙房称了一百斤大米和几斤咸萝卜干,跟连队借了一口比较大的饭锅,每人牵一头脖子上已挂着“牛拖”的大水牛向着深山出发了。 (牛拖是用两条粗约八九厘米,长约三米半且非常结实的黄牙木做主杠,主杠的一头在距离尾端约一米处用一条长约七十厘米的横杠用榫口接驳的办法横着把两条主杠连起来,横杠在接驳之前已套入两个用十二厘米直径做成的活动铁环,形成一个工字。前端用一种十分坚韧叫牛肶藤做成的约七十厘米长的粗绳子把两条主杠连起来,把连在主杠前端的“牛压”挂在牛的脖子上固定好,把木料的一头放在横杠上利用铁环绑好,并打上马钉卡紧后,牵着或赶着牛走就可以把山上的木材拖到山下) 记得参加这次上山伐木的人员有罗定的老工人蓝春成,广州知青李仲勋、罗士成和我傅耀新,潮阳青年黄林松、陈炳泉、谢同发。共计七个人。 我们曾提前去做好了准备工作;为方便用水,我们就地取材,在半山腰一条水沟附近搭建了一间简陋的小茅房,平整地面后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刚砍下的芒草,以避免直接把草蓆铺在潮湿的泥土上,在小茅房的四周开挖了排水沟,扎上了坚固的木围栏以防止晚上有野生动物闯入,为免晚上被吸血的山蚂蟥叮咬或受毒蛇和蜈蚣等动物的伤害,我们在小茅房的四周撒上了农药和硫磺。 经过近三小时的路程,我们到达了此预定地点,大家把牛带到草地吃草后便忙于在小茅房内整理“床铺”蚊帐等。从这天的下午开始,我们便投入到紧张的伐木工作中。 地处热带亚热带的海南岛,连绵不断的高山上生长着无数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树龄的参天大树,要找到连片的适用树材只能凭经验,我通过爬上树顶向四周观察,从树冠的生长形态判断,很快就找到了一片位于大半山腰中的上好树材——海南杉,这种高大的乔木植物不但有长得笔直和体轻、易砍伐的优点,而且有一种天然的药油味,蚊、虫和白蚂蚁都不敢接近它,是用作建房子的桁条、桷子板的上好材料,经过十多天的共同努力,我们把几百棵海南杉都放倒了, 可是,比砍伐海南杉艰苦得多危险得多的大型实木砍伐工作还在后头。 为了与阳光争时间,我们白天都是拼命地工作。在原始森林中,由于高大茂密的树冠把太阳光遮蔽得严严密密的,给人的感觉是一天里只有短暂的几个小时是白天,到了傍晚六点钟左右,整个森林都处在一片漆黑中,让你无法行走。下班后也只能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在山溪中洗去一天的疲劳,晚上大家屈膝盘坐,围在一盏煤油灯下研究一下第二天的工作后,就是打打扑克牌。工作是十分的繁重,生活是无比的艰苦和枯燥,每顿吃的都是粗米饭加咸萝卜干。为了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在进山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我和广州知青李仲勋趁着回连队拿大米和萝卜干的机会,顺便把两支“东方红”汽枪和一把吉它琴都带上了。 深山老林里繁衍着无数各种各样的鸟类,在这杳无人烟的地方,小鸟近距离见到我们竞然一点都不害怕,我们只是在小茅房门口吃完午饭的半个小时内提着汽枪随便转转也能打到几只,运气好的话可打到十多只。被打到的多数是‘海南鷯哥’鸟。不是我们天生就喜欢杀生,而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只好牺牲它们的生命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晚上,我们依然围坐在那盏煤油灯下,一边弹琴一边唱歌,琴声和歌声在漆黑寂静的山谷中发出阵阵的回响,我们的生活从此得到了改善。但为了这件事,当时身为农场干事的曹博文在一点真实情况都不了解的前提下竞大做文章,到处讲我们的坏话,特别是在场部一带散布:“十七连的广州知青工作态度不端正、资产阶级思想极其严重、每天上山备木料都是一边弹琴一边赶着牛跑”等等等等, 与本文无关并曾经扬言要对我们进行批斗,所幸的是不知为何到了后来却不了了之,或许是受到良心的责备吧。 这次我们主要采伐的树材有:黄果、香春、山枣、花星、红犁、白犁、青梅、香樟等,这些都是上好的木材。规格要求:直径要达到三十厘米以上,树身要直,(直径太小或树身弯曲都会影响出材率)树被放倒后要用锯把它截成两米二到两米三长。 砍伐大圆木是件既辛苦又危险的苦差,这对于一个完全没有伐木经验的人来说,那简直就是在玩命。在茂密的热带森林里,人迹罕见,树木参天,到处都生长着满身带刺的植物,一不小心将会令你疼痛难当,比碗口大的过江龙藤、鸡血藤、大血藤、加上一些叫不出名的各种藤类植物互相攀爬互相缠绕,在大树与大树之间编织成一张张天然的藤网,而令伐木工人在一舜间遭受伤害甚至失去性命的罪魁祸首正是这种天然藤网。我这里说的并不是藤网会主动攻击人类,更不是像神话小说里说的有什么妖魔鬼怪。在我八年的知青生涯中,进山备木料的时间合计也有三年多,亲眼见到过不少危险的镜头。记得那是一九七0年的事了,当时我在武装连,在全团学习武装连,武装连向全团学习的号召下,武装连包下了“娘子军连”在新建连队十三连的所有开荒任务。 一个寒冷的上午,天下着蒙蒙细雨,战士们仍身穿雨衣不知疲倦地挥舞锄头和砍岜刀战斗在山林里。作为班长的我,除了要完成自身的开荒任务外,更重要的是必须随时随地掌握着工地的各种情况,突然,一幕危险的景象出现在眼前:几个没有经验的新战士把身边的几棵大树都砍断了,但树却没有倒下,而是呈四五十度角倾斜地被吊着,是那些天然的藤网把这几棵树不规则地吊在一棵直径约四十厘米粗的大树上,粗壮的树杆已经被压得啪啪作响,可是毫无经验的他们却一点也察觉不到灾难即将发生,他们仍站在危险区里。看到这情景,我忙不迭地高声呼叫他们马上散开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几棵大树轰然倒下,那几个新战士被眼前的景象直吓得目瞪口呆。 另一次是发生在以上所说的采伐大圆木的日子里,这一次我虽然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又有谁会料到直径粗达五十多厘米的一棵大树只被我砍了一刀就轰然倒下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更没有天生的神力和宝刀,其实也是那些天然藤网在作怪;记得这天的事情是发生在中午十二点左右,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但还不见两位潮阳藉的青年回来,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我提着砍刀急急赶往山坡的另一面查看情况。原来是他们遇到了麻烦。黄果树的树梢长得高,而它向四周延伸的分枝也长得十分的粗壮,缺乏经验的两人已经把位于它下方的七八棵可用的大树都砍断了,(砍伐树木应按树身的生长状况选择下刀的位置,以达到树木倾倒的方向满足伐木者的要求)。结实的藤网却把它们牢牢地吊在这棵黄果树的几条分枝上。这棵树生长在约三十五度的斜坡上,树的下方有两棵直经约二十厘米的杂树挨着,距离它上方八九十厘米是一块露出地面约有六七个立方米大的石头,沉重的压力已把这棵黄果树的树杆压得微微弯了腰,伐木的人最怕就是遇到这种最危险的情况。怎么办?是放弃这几根好木材还是想办法把它们都要回来呢?放弃的话不但浪费了时间,而且浪费了好木材,反之却又十分的危险,经过反复考虑后,我终于决定了不放弃。把两位潮阳青年叫离危险区后,我一个人提着大砍刀走到了这棵大树的右边,由于在树的下方无法下刀,只好伸长双手向大树的外弯处砍去,只听到一声巨响,已被压弯的树杆在这一刀之下舜间折断,在强大的作用力下,树杆似出膛炮弹的速度擦破了我手臂的皮肤后撞向大石,被吊着的几棵大树也同时倒下了。多么惊心动魄的一幕啊,在这一舜间,我算是在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 17连部分知青当年在连队的合影作者:傅耀新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axuetenga.com/dxtrybw/13600.html
- 上一篇文章: 农村人称鸡屎藤,名字虽不雅,做成美食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