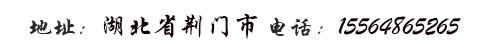我家葡萄徐长成下
|
北京专科皮炎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a_yufang/210112/8582670.html十从宣城到京城,两月脚程,快马加鞭不需半月。徐訢坐着马车晃晃悠悠,竟走了三月有余。“什么时候到京城?我快要吐死了!”花精气若游丝。葡萄藤是徐訢离家时 亲自动手收拾的“行李”。现如今枝叶恹软地耷拉着,半死不活。起初徐訢还有余力心疼一下,时间久了他自己也遭不住折腾,整个人无精打采地躺着:“要不是带着你,我早在京城吃香喝辣了。”“那你把我放在这路边,我用藤蔓爬到京城也比现在强。”“别闹了,小祖宗。”徐訢终于挨到了京城,一见城中青瓦石砖,宝马雕车满路;酒肆茶楼,花旗招展乱眼。整个人顿时来了精神,也不先找他爹,直奔着最繁华的酒楼去。啃了三个多月的干粮,他得先找点人能吃的补补。一落座,徐訢顺着牌子,从左到右点个遍。店里的伙计眼珠子转了转,脸紧嘴严,迟迟不言语。徐訢知道,这是嫌他风尘满衣衫。他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正直了身子骨道:“给我升雅座,刚才点的菜,一刻钟内全部摆上!再把门外拴着的马车牵到后院喂饱,车里有一盆葡萄藤,放到阴凉处,好生照顾!”伙计见着银子,立马换了满脸的褶子笑:“好嘞客官,二楼请。”酒楼名为聚贤楼,二楼窗户临湖,有烟水楼台,绿柳成荫。室内很宽敞,却只设几副桌椅,错落有致,且都有浮雕屏风挡着,果然清雅许多。旁边几位见有人来,不禁多打量几眼,尔后讥笑道:“如今什么人都能来聚贤楼现眼了。”“看样子是进京赶考的书生。”“平日好好的京城,最不爽利的就是这几个月,被一群穷酸秀才搞得乌烟瘴气。”徐訢知道这顿饭吃不称心了。宣城家喻户晓的徐家公子,口口相传的天才神童,半死不活地赶到京城,可不是受这闲气的。“平日好好的饭菜,眼下被一张臭嘴搞得臭气熏天,确实最不爽利。小二,倒了重做!”这话是故意说给隔壁听的。如他所愿,其中一人气急败坏地冲出来:“你骂谁呢?!”徐訢扫了他一眼,这不明摆着呢吗?来人被徐訢的轻视惹毛了:“无籍鼠辈,初来乍到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无籍鼠辈?”徐訢感到好笑,“两个月后,满京城的人都得知道我名字!到时候你也得在旁边看着本少爷骑马游街。”说完也不恋战,拂袖而去,“呵,好好的京城?饭都吃得晦气!”余下几人脸上一阵青红皂白。座间一个老者终于开口:“去查查这人什么来历。”另一人道:“不用查了,户部侍郎徐祈哲的儿子。我去年在宣城亲点的解元。”“老师怎么会选他?”刚和徐訢打嘴仗的人惊讶。老者也斥道:“糊涂!你怎敢点一个有父在朝的人做解元?日后查起来……”“我也是事后才知道。不过他的卷子议古论今,纵横开阖。即使圣上来判,解元也当是他。”“他今日作派你也看见了,会试自己掂量着办!”“是。”十一徐訢一到侍郎府就被他爹禁足,美其名曰: 冲刺。徐訢不屑:“你不过是怕别人知道我是你儿子,今年会试受阻罢了。”徐祈哲道:“别管我怕不怕,你静下心多读几日书总没错!”可惜他不知道,徐訢一进城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不过徐訢自己也不知道。他依旧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以笔为矛,指点江山。然后一身轻松地离开。不久之后放榜,明晃晃的太阳照在尺牍长宽的榜单上,照得他有些眼花,翻来覆去看了百遍,就是找不到“徐訢”两个字。旁边有人认出他:“这不是在聚贤楼大放厥词的小子吗?榜单上哪栏是你大名?指出来我认认?”徐訢也认出是那日发生口角的人,心情本就不佳,此时目光开始有些阴沉:“你怎么知道榜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你知道我是谁?”他眼神一紧,步步紧逼:“你又是谁?”那人还不待回答,旁人插嘴道:“他你都不认识?这可是翰林院最年轻的学士,大名鼎鼎的高翰林!”徐訢忽然笑了:“所以我今年才会榜上无名?”高翰林急道:“你上不上榜与我何干!自己才薄德浅,还赖上别人了!”徐訢被戳了心窝子,考场失意的事实本就让少年的一腔热血在五脏六腑突突乱窜,如今被人一挑拨,一下子喷薄而出。他眼神冒火,直勾勾地盯着高翰林:“你!”又一伸手,食指指向榜单:“还有李濂、杨修杰、陈泽,敢不敢和我比试一回!”他念的三个名字的是今年新科状元、榜眼、探花。此话一出,众人一下子沸腾了。百十人把他们拥成一个圈。榜单三甲原本混在人群中,此时被人推拥出来。其中两人还沉浸在金榜题名的巨大喜悦里,不想掺和这事。白纸黑字,已宣告天下,何必再徒惹是非。独探花未表态,望向高翰林,一副为他马首是瞻的样子。看来已经开始谋算日后的锦绣前程。高翰林本不用理他,但那日老师一句“即使圣上来判,解元也当是他”始终让他耿耿于怀。当年殿试,他洋洋洒洒,一炷香七文,风光无二。可见到徐訢 眼,他便不自觉地穿盔戴甲,唇剑舌枪,那是同类才能嗅到的危险。就如今日他名落孙山,也是一身倨傲,像他当年殿前题名一般。“好!”高翰林挑眉,冷笑道。人群爆发一阵惊讶,任谁也没想到高翰林会应下来。一时间,落榜书生要挑战当今翰林的事情传遍大街小巷。众人挤拥着往聚贤楼去,路上不断有人打听怎么回事,知道了便加入。如此熙熙攘攘,浩浩汤汤,等到了地方,酒楼外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店主忙派几名伙计拉成一道人墙,好让高翰林他们进去。徐訢、高翰林、探花等人到了二楼,文书四宝备齐,众人落座。十二文人宴会时多吟诗作对,以赋雅兴。但今日三人争得是国士之名,而非风花雪月。自然舍了诗词歌赋,也略去琴棋书画,专注“经论”。楼下看客推举出十位文人,各出一题,店主抓阄,三人现场作答;在场人士皆可阅览,举人以上方可投票评选。店主左旋右悬, 抓出一张纸条,论“无为而治”。探花略一沉吟,提笔而著。高翰林看徐訢把手放在两腿之上,眼睛虚望着窗外,没有动笔的意思。他顺望去,数年如一年的烟柳楼阁,不知有什么意思。感觉他不过虚张声势,冷哼一声,不再等,也拿起笔。比试开始了,楼里楼外数千人,窸窸窣窣,店小二提着水壶轻车熟路,鱼贯而行,没有洒出分毫。迟迟不动笔的徐訢打量着窗外,看客打量着他,交头接耳,“怎么还不动笔?”“怕露怯?”“定是怯了”。徐訢充耳不闻,多年以后,身在京城,他回想起父亲带他种葡萄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若由着它的性子……只会瞎长疯长……爬一园藤颗粒无收。”自小父亲教他修身养性,这是“有为”,多年来他奉为圭皋。抛去年少无知的三年叛逆,纵是天资聪颖,他也每日手不释卷,不敢懈怠。‘无为而治’是老子给出的治世之策,初读时他觉得艰涩难懂,夫子释义后他又觉得于理不合,不过一家之言。但年岁渐长,他在后花园的一草一木抽芽、结果、碾成泥的过程中看见自然的力量,明白了“道法自然”,也明白了“无为”是顺应自然,尘归尘,土归土,不干涉,真自由。其实无论“无为”还是“有为”,都只是手段,目标都归于“更好的实现道”。想明白这些后,即使他自认为在才学上已比肩父亲,也依旧顺应“自然”秩序,进京考取功名。只是他为道“无为”,他人为私“有为”,如今“无为”“有为”的对决中,他的“无为”败下阵来,“道”不能现。这合理吗?合情吗?徐訢越想,心血越是翻涌上升,终于,他从窗外收回眼神,挥笔泼墨,一蹴而就。“动笔了!动笔了!”看客们一阵骚动,转即又归于安静。太阳已收了耀眼的光,血红红地挂在天上,铺了一河的血缎,烧得每人脸上*灿灿。空气被成百成千的人群拦住了,丝毫不动,裹在其中的汗臭味实在难闻,人们却浑然不顾,目不转丁地盯着楼上三人,仿佛自己的*也在奋笔疾书。小厮们将已写好的纸张拿下楼,三个老先生用大字誊写。文章先是破题,探花引前人之言,老生常谈;高翰林回归《道德经》,以经释经,很是严谨。 出来的徐訢,却言自家草木,众人看了摇头,“气象小了”。小厮们拿出来一张,人群便喧嚷一番。楼上徐訢不为所动。不一会儿,探花落笔,弓手下楼,在一旁饮茶歇息等待。高翰林正写得酣畅,不时喊“纸来!”“纸来!”留在他文章前的人也最多,称赞声不绝于耳。再看徐訢,气定神闲,运笔游刃有余,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他起笔言一草一木,再接一国一民, 大讲特讲道法自然,文章渐入佳境,留足细品的人也越来越多,方才说“气象小了”的人不禁脸红,自此噤声。还剩 “余意”部分。众人翘首以盼,人群比刚开始更挤了,前几排的人几乎双脚离地,被架起来。只剩 一页了!忽然人群乱起来,纷纷闪开。两顶官轿被人抬着疾步而来,众人纷纷交谈,这是翰林院大学士,高翰林的师父;还有一人呢?看着眼生。但也有京城百事通,眼尖的率先嚷到:“是去年新任的户部侍郎。”徐訢刚写完“无为乃术,道乃本源,道法自然,自然而为”。正要落笔就听见他爹的大名。待抬头时他爹已冲到眼前,突然眼前一黑,他爹一巴掌掴来,“回家!”另一边的翰林院大学士也没好脸色,重重地冲着高翰林哼了一声,甩袖而去。高翰林急匆匆地跟上去,走时还不忘扫了徐訢桌案一眼。徐訢怨怼地看了眼徐祈哲,快步走开。一阵轰轰烈烈的经论大赛,就这样闹剧收场。晚上,父子两人坐在花园假山旁。石桌上一壶葡萄酒,酒体通透,在月光下泛着红宝石光泽,可惜谁都无心饮酒。徐祈哲一脸愠色:“你今日闹出这般阵仗,以后还如何同朝为官!简直是自断前程!”“那不做官便罢!”徐訢*气道。“混账话!”“他们徇私舞弊,因与我有口角冲突,便作梗打压。这事你不问,倒先怪我正大光明的与他们比试!”徐訢越想越气,真真的是非颠倒到家了!“你可有证据?无凭无据,告到天王老子那也没有!”“你去向考试院要我文章!一看便知!若比不上状元文章,我立马收拾行李回宣城!再不进京城半步!”“什么话!多大了还像孩子一样*咒发誓?!都是你娘惯的!”“骂我就骂我!好端端的攀扯我娘干什么!” ,父子俩不欢而散。徐訢留在原地良久,将杯里的葡萄酒一饮而尽,怅然道:“好不容易从宣城带来的葡萄酒,他也没喝一口。”“给我斟一杯。”花精摇了摇藤蔓。“呵呵,虎*尚不食子。你真要喝?”“什么虎*不食子,相煎何太急,不过是你们人类拿自己的礼数揣测万物。”花精不屑,“这果子若不酿成葡萄酒,也要落到我脚前, 成花肥。不正是你说的‘自然之道’!”徐訢被她一本正经的胡诌逗笑,抬手往她藤根上浇了一杯。花精喝完心满意足地感叹:“京城的水土,怕难结出这么甘甜的葡萄。”“想家了?”徐訢问。“你不想吗?”“想。”“我们回去吧。”花精趁机提议。“再等等,我还有事要办。”十三这一等就是三年。自那日聚贤楼大赛后,徐訢誉满京城!当日虽然两位当事人提前离席,留在桌案上的纸张还是被人誊写完整,当时在场的举人五五站队,没有决出胜负。但过不多久京城识字之人几乎人手一份,交相传诵的皆是徐訢之文。就这样,徐訢凭着真才实学,在京城打出了任谁也驳不倒的天才名声。三年后,徐訢在万众瞩目下再次走进考场,顺利通过会试、殿试,成为钦点状元。而徐祈哲也没有被言官弹劾。因为徐訢才华太盛,名声太大,以至于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他不是今年的新科状元,一定是考试有问题!自夺魁后,徐訢开始深居简出,浑然不像前几年的作派。这日他来到书房,想与他爹商议日后之事。他已打定主意,向圣上请辞回宣城,人亲地熟,最是快活。刚要进门,听见书房有声音,他停了下来。“徐大人这封奏折还是再思量思量吧。”来客声音尖得刺耳,“海南战事吃紧也不是这一天两天了,你在那几年最熟悉不过。圣上的陵墓却是千秋万代的大事,谁耽搁得起?”是宫中的人,怎么没有通报?徐訢边听边思量,海南?陵墓?听起来像是近日朝堂上热议的修皇陵一事。徐訢听说前不久挖出了石头,相关官员都被弹劾问责,之前花费也都打了水漂。如今内务府想法子筹银选址重修,大臣中有人反对,看来他爹就是其中一员。恐怕还是相当重要的一员,才劳圣上特派人来府,逐一瓦解。“杨公公所言,本官不敢苟同。黎民百姓,也是社稷之本,千秋万代的大事。”“呵,一口一个为国为民,你拍拍你的心窝子,当真是为了百姓,还是为了博个直谏的贤臣名声?!”来人喝道,说完语气又软下来,“这话是圣上一字不落让老奴带给你的!”“上书陈情,是微臣之职。体察民意,是圣上之德。徐祈哲不敢有点私心,望圣上明察。”待宫中人走后,徐訢走进书房。徐祈哲刚经历一场硬仗,此时正靠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海南匪乱,当真如此紧张?”徐訢问道。他爹在福建监*期间,他没少收集那边的情报。“你也怀疑我别用有心?”徐祈哲冷冷道。“儿子不敢。”“你来找我何事?”“我无意为官。所以过几日圣上召见,我打算向他请辞。”“你不做官,要做什么?”徐祈哲惊得睁开眼。“还不知道,我再想想。”“胡闹!”“我心意已定,只是跟你打个招呼。”“你敢?”“功名是我考的,嘴长在我身上。”“混账!”又是一场不欢而散。徐訢独自一人在院里刨葡萄根,不让旁人插手。花精在他耳边叽叽喳喳,好不兴奋:“我们真的能回去了吗?你真能舍了高官厚禄?”“有什么舍不得的。盛世为官不过图个虚名。”下午在书房听到的对话,让徐訢对他爹仅优于他的数十年阅历也不仰慕了。官海浮沉数十载,到头来也不过沽名钓誉,这官做着有什么意思?“你想办的事也办完了?你办了什么事?每日跟一群文人吃吃喝喝? 考个状元?”花精好奇。徐訢边挖花精的根,边解释,他这三年在京中,并没有像他爹说的那样韬光养晦,而是不拘天性,不掩盖自己的才华名气,将之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任其在京城流传膨胀。 任何人也不敢逆人心,在他考卷上做手脚。这是他想到的,用“无为”为自己找回“公道”!徐訢说得起劲,丝毫没注意到身后有人。花精连连咳嗽提醒,嗓子都咳哑了,徐訢才回过神。是徐祈哲。他本想来劝徐訢回心转意,无意中听到他这番大论。徐祈哲和徐訢面对面坐着,良久无言。徐祈哲打量着被徐訢刨出一半的葡萄根,先开口说:“初见时它还只有豌豆大小,如今根茎都这么粗壮了。”“十多年了。”说到葡萄藤,徐訢语气不自觉地柔和下来:“年年结果,在宣城出了名的甜。”“记得种它当日,我教你要好好修剪枝条。”“是,这些年一直如此。”“是吗?刚刚还有人说不拘天性。”徐訢一愣,思忖道:“父亲教训的是。儿子确实不该为了口腹之欲,年年委屈了她。”“我是这个意思吗?”“是儿子自己悟出的这个意思。”徐祈哲盯着眼前人,不知什么时候,徐訢已变成眉眼刚毅,轮廓分明的成熟模样,而他竟然刚刚才留意到。他叹了口气:“你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很正常。只要将来不后悔就行。”“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哈哈哈~朝闻道,夕死可矣!好啊!”徐祈哲大笑:“给我倒一杯葡萄酒,我尝尝是不是如你所说的那般甜。”徐訢取来酒坛,郑重地给徐祈哲满上。两人推杯换盏,你来我往,不过半柱香,酒坛就见了底。徐訢醉倒之前,隐约听见徐祈哲说:“海南虽有匪,却不敌我心中魔啊……”最终,徐訢快马回乡,朝着道法自然的人生一路狂奔。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axuetenga.com/dxtpzff/10323.html
- 上一篇文章: 鹿茸怎么泡酒鹿茸泡酒有什么作用
- 下一篇文章: 特殊兵种分析青州兵无当飞*很强,虎